寧靜像是一種錯覺,而嘈雜仍無處降臨——
林鴻文與「聲稀之於—2013作品展」
文|陳寬育 2013,08
觀看林鴻文的畫作,在那些由滴流、堆疊塊體與整體顏色沉穩的畫幅中,有多種能量型態正低調地閃現,那樣的張力有點像是闇夜照明彈的生滅;發射時的爆炸性閃亮、殘留於槍口的燃燒痕跡、黑夜中的白色煙幕、高懸空中時顫動的光影、即將墜海熄滅時對於黑暗再臨的恐懼等待、黑暗再度籠罩時視網膜的殘影。也許這種比喻是很視覺性的,但那種爆發後的時間性,以及對於這段「光照」過程的記憶與體驗之再現,頗能標識與林鴻文創作有關的幾個因素。
與其說林鴻文的繪畫追求某種穩固法則的構圖布局,不如說追求的是對各種「肉眼」與「心眼」觀看經驗的再臨。儘管對繪畫的教養讓我們熟練地想被吸納其中閱讀那些意象,卻發現流動於畫中的能量狀態穩穩地沉澱在物理支撐的畫幅表面,對深度的想望也似乎被畫布的物質基礎給橫阻在前。因而,與其說這是繪畫吸納性的深度暗示,毋寧說這裡有著經由展覽中多件作品共構而成的「境」。
事實上,林鴻文的繪畫作品經常被置入某種抽象繪畫的脈絡來討論,而其立體與裝置型作品也往往被理解為具有環境藝術的關懷向度。但也許可以說,這其中對於「境」的執著與瓦解,正是林鴻文多年來透過諸種創作手法所欲企及的。面對林鴻文的作品,如果說其藝術上的創作嘗試是從當兵部隊中的影印機開始的,似乎也自成一個探討其生涯藝術實踐的有趣進路。
1980年代初,林鴻文在某些機緣下開始以影印機「製造」圖像,也曾有一段短暫活動於重慶南路的創作時光;那是流連於影印店與明星咖啡館,分別以手繪和機器印出之間的各種圖像型態組合可能性的明亮時刻。這些對於繪畫性與抽象性的實驗,隨著1983年起歷經參與今日台北雙年展前身的「中國繪畫新展望」展,以及1984年獲得雄獅美術新人獎等鼓舞後,林鴻文選擇回到台南繼續其創作生涯,而南台灣廣闊的生活環境也讓早已悄悄萌芽的,對於環境藝術的想法開始茁壯。
關於林鴻文,「深度的旅行」可能是最真切的理解方式。所謂旅行不只意指其身體之位移與漂浪——無論是在山中、海上、台灣森林、異國湖畔的身心感受經驗,更是一種面對世界之觀點的不斷推移。這樣的狀態就像是將那現實中的不合理與超現實情狀轉化為某種養分般的能量形式,並在對事物的重度凝視,對細微之物的深情描述,以及對文字語言的雕琢凝鍊之中,以逃逸之姿回返心中的原初之境。也就是說,人們被其繪畫、雕塑、詩文與環境裝置中發散出的微微光暈所罩染的,是其旅程中的暈眩疲累、闔上眼睛的光點、夜闇的沼澤森林、火山口清晨的湖光與向湖面流洩的雲。儘管人們在作品中看不到具體的形象,其實卻已全都展露在眼前。當透過作品參與並分享那交融的既視感與未知感,倒也頗有某種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式的味道:在對物事的觀看中,卻有以有限包含無限,親臨所有的時間、空間與無限世界之感。
關於世界之隱喻、視覺進出所暗示的肉身疲憊,以及藝術家虛構的袋蟲故事以「囊袋式」的作品意象不斷出現,伴隨著林鴻文一路走來。在靜謐的觀看感受中,人們以意象重疊意象,也終於察覺到聲音的細微震動,而那其實是一場跨越數十年的唱和。當回到1980年代重慶南路的影印店以單調的重複嘈雜規律地印製待組裝的圖像,1990年代至今藝術家穿梭於大自然中的荒野聲響,也來到2010年代的鋼鐵廠房(或藝術家的工作室)裡,焊接機將金屬隨機且炙烈的穿破熔合的高溫詭鳴;這些總伴隨著作品生產過程的持續嘈雜,卻也造就藝術家創作時心中最寧靜與柔軟的狀態。
只是,作品所交織的寧靜與嘈雜,不易指出何者壓迫另者更多。其實回顧林鴻文的創作歷程看來,這關於聲音的兩組概念之相對性,也一直處於潰散狀態。當被吸納入林鴻文展覽的「境」中,會發現寧靜像是一種錯覺,而嘈雜仍無處降臨。兩者均在場,但無處追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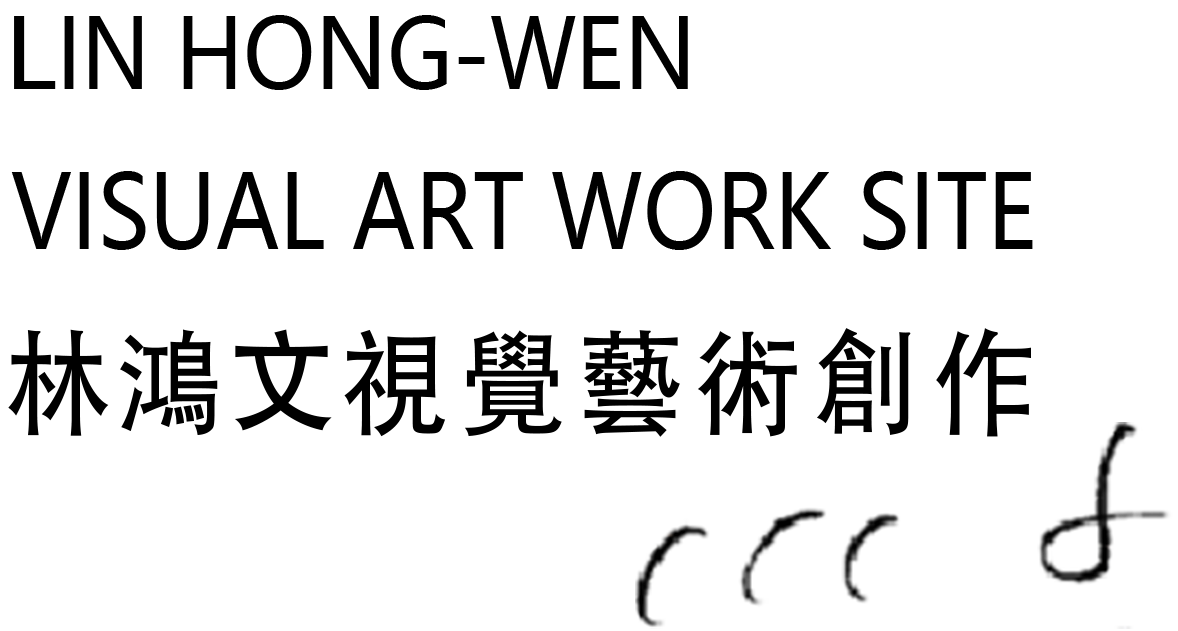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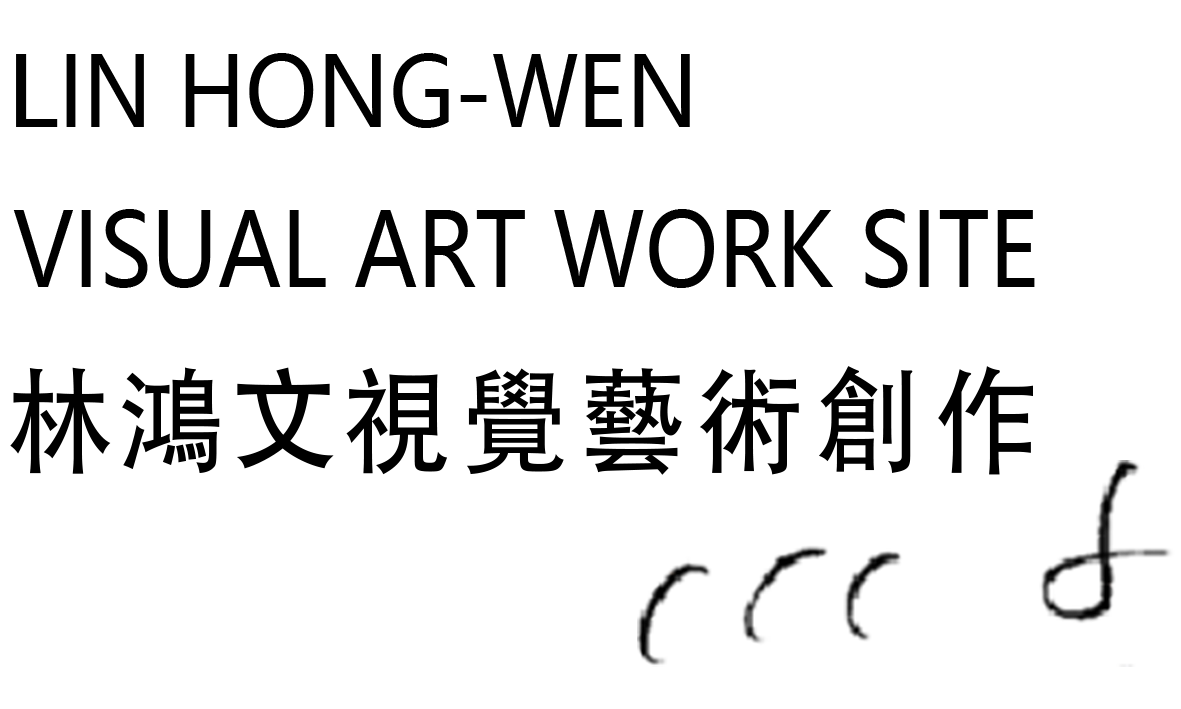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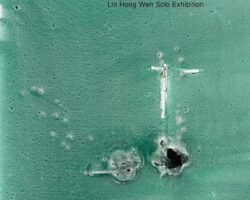


No Comments